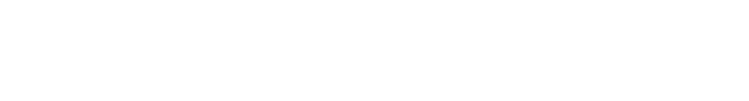中文标题:探索制造业的AI应用:人工智能采纳准备度的影响
英文标题:Exploring AI adoption in manufacturi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effects of AI readiness
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发表时间:2025年7月
作者:Heidi Heimberger, Djerdj Horvat, Angela Jäger, Frank Schultmann
引用格式:Heimberger, H., Horvat, D., Jäger, A., & Schultmann, F. (2025). Exploring AI adoption in manufacturi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effects of AI readi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109733.
一、摘要
尽管人工智能(AI)在制造业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许多企业仍对全面应用这一变革性技术犹豫不决,其AI整合准备度令人存疑。现有研究虽已开始探讨AI准备度与AI应用之间的关系,但相关实证分析仍显不足。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从技术和组织双重维度,探究了企业AI准备度(单独及协同作用)对制造业AI应用的影响。基于德国制造业调查的1334家企业数据,我们通过描述性统计与多元分析发现:企业需同步提升技术与组织层面的AI准备度,才能有效推动AI应用。然而,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矛盾——制造企业虽表现出较高的AI准备度水平,却仍对在生产流程中实施AI持谨慎态度。研究还表明,不同企业在AI能力建设上采取了差异化策略。更重要的是,分析结果凸显了企业间存在的显著差异,某些企业特定特征对AI应用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尤为有趣的发现是:企业规模与AI应用呈U型曲线关系,而产品复杂性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研究背景
制造业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AI)技术作为其中一项颠覆性工具,正日益受到关注。尽管AI在制造业中具有提升生产效率、灵活性和自动化水平的巨大潜力,但目前其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仍然处于较初级阶段,许多企业对全面采纳AI持谨慎态度。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与业界对“企业是否具备充分的AI采纳准备度”这一问题的质疑与讨论。
三、研究空白
目前,已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初步建立了AI准备度与AI应用之间的理论联系。一些学者基于技术应用模型(如TOE框架、Diffusion of Innovation模型),分析了影响企业应用AI的关键因素;也有研究将AI准备度视为一种资源基础,涵盖了企业的数据基础、IT基础设施、员工技能、创新文化与合作能力等方面。这些工作为理解AI应用提供了宝贵视角。
然而,这一领域仍存在显著的研究不足。首先,定量实证研究较为稀缺,尤其缺乏基于大样本的统计分析,难以得出具普遍性的结论。其次,大多数文献缺少对“AI准备度”向“AI应用”转化机制的清晰解释,即企业拥有资源准备是否真正促成了AI的实际部署,这一中间环节仍不明朗。此外,已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整体企业数字化,而较少将分析场景具体限定在制造业的“生产流程”中,导致研究结果难以指导实践层面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当前关于AI准备度大多采用“统一评分”视角,忽视了其“技术”与“组织”两个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与组合效应。
为填补这些空白,本文旨在回答以下核心研究问题:
企业的AI采纳准备度如何影响其在生产流程中应用AI技术的可能性?
四、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AI应用理论
AI应用研究延续了技术创新应用的经典理论脉络,该领域长期关注影响组织应用新技术的过程与因素。早期研究包括组织层面的创新应用过程分析(如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以及Tornatzky和Fleischer提出的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以及个体层面的技术接受模型(TAM)、理性行为理论(TRA)、计划行为理论(TPB)等。
在组织层面,TOE框架被广泛用于IT创新应用分析,并被扩展到AI应用情境中,用于将影响因素分类为技术、组织与外部环境维度。现有研究已探讨了AI应用的具体因素,如技术基础设施、人员能力、流程整合等,但制造业尤其是生产环节的跨行业实证研究仍然稀缺,且较少同时引入“AI准备度”概念进行分析。
2. AI准备度理论
AI 准备度的理论根基在于组织变革准备度(Organisational Readiness for Change)与资源基础观(RBV)。
组织变革准备度理论强调,组织内部共享的心理与实践状态决定了其是否愿意并有能力实施变革,这取决于组织的内部能力、沟通水平、员工参与度与目标认同感。高水平的变革准备度有助于创新的成功应用。
资源基础观(RBV)则强调,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对稀缺、难以模仿且能创造价值的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如 IT 基础设施、数据平台)、无形资源(如企业文化、知识积累)以及人力资源(如员工技能与管理能力)。
在 AI 语境下,RBV 被扩展为“AI 能力”框架,指企业整合和利用 AI 特定资源的能力。AI 准备度因此包含:
技术性AI准备度(Technological AI Readiness):有形资源,如数据可用性、IT 基础设施、安全保障。
组织性AI准备度(Organisational AI Readiness):无形与人力资源,如员工技能培训、创新文化、合作意愿。
五、概念框架

图1 理论框架图
研究假设:
H1:制造企业的技术性 AI 准备度越高,其在生产环节应用 AI 的可能性越大。
H2:制造企业的组织性 AI 准备度越高,其在生产环节应用 AI 的可能性越大。
H3:综合 AI 准备度(技术+组织)对 AI 应用的正向影响强于单独的技术性或组织性准备度。
六、数据与方法
1.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German Manufacturing Survey (GMS) 2022,该调查始于 1993 年,每三年一次,自 2001 年起成为欧洲制造业调查的一部分,长期用于分析企业在产品、工艺、服务及组织创新方面的特征与变化。选择德国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德国是工业数字化的早期领军市场,制造业竞争力在全球具有示范作用;另一方面,2022 年正处于 AI 技术(如语音识别、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在工业应用快速扩散、并受疫情推动的重要阶段。本次调查覆盖 NACE Rev. 2(10–33 类)下雇员 20 人及以上的制造企业,问卷由生产经理、首席技术官或生产设施总经理填写。调查于 2021 年秋至 2022 年春以 push-to-web 方式进行,按行业分层随机抽样,共抽取 15,299 家企业(净样本 13,252 家),最终获得 1,334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10%),样本在区域分布、规模和行业结构上具有代表性。本研究使用其中 1,130 家在 AI 准备度、AI 应用及企业与生产特征等变量上数据完整的企业,样本与排除案例在关键特征上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2.在变量设定上,因变量为 AI 应用,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具备自学习功能的软件系统,涵盖生产过程管理、质量控制、设备维护和内部物流管理四大应用领域。自变量为 AI 准备度,包括技术性与组织性两大维度:技术性准备度涵盖数据可用性、IT 人员比例和数据安全措施;组织性准备度包括数字技能与沟通工具、员工培训、创新文化和外部合作。两者加总形成综合 AI 准备度,并分为五个等级。控制变量涉及企业结构特征(如员工规模、行业类别)及生产特征(如产品复杂度、批量规模、价值链位置)。
3.在方法上,研究首先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组间比较,利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检验评估不同 AI 准备度水平下 AI 应用率的差异。随后采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检验技术性、组织性和综合 AI 准备度对 AI 应用的影响,并控制企业与生产特征。为确保结果稳健性,研究检验了多重共线性、异常值影响,并按企业规模分组进行拆分分析,结果显示模型估计稳健可靠。
七、研究发现
Finding 1
尽管德国制造业企业整体 AI 准备度(包括技术性和组织性资源)水平相对较高,但在生产环节实际应用 AI 的比例仍然很低,仅约 14%。许多企业在具备较强技术和组织条件的情况下,仍对 AI 的使用持谨慎态度。
Finding 2
同时重视技术性与组织性资源、形成整体性 AI 准备度的制造企业,在生产中实施 AI 的可能性显著更高。
Finding 3
AI 应用显著受企业的结构性特征影响。制造复杂产品的企业,尤其是处于高度专业化行业(如汽车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 AI;而批量规模和价值链位置对应用影响不显著。
Finding 4
企业规模与 AI 应用呈 U 型关系:大型企业和非常小的企业应用 AI 的概率均高于中型企业。在复杂产品制造中,这种规模差异更为明显。
八、管理启示
理论贡献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RBV)与组织变革准备度理论,提出了一个分析制造企业 AI 应用的框架,将 AI 准备度划分为技术性准备度与组织性准备度两大维度,并进一步构建了一个五级有序指标(从无准备到高度准备),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可操作且细化的测量工具。研究不仅填补了 AI 准备度与 AI 应用之间中间环节的实证研究空白,还揭示了企业在不同规模与结构特征下构建 AI 准备度的差异化策略。例如,小型企业更倾向于加强组织层面的变革管理与员工准备,而大型企业则依托更成熟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提升技术性准备度。此外,本文还发现企业规模与 AI 应用呈 U 型关系,并且产品复杂度会强化 AI 准备度对应用的影响,为理解结构性因素在 AI 实施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实践贡献
研究结果对制造业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具有直接指导意义。首先,尽管许多企业具备中高水平的 AI 准备度,但在生产环节实际应用率依然偏低,这提示管理者需在技术之外注重组织层面建设,例如提升员工认知、推动内部试点项目。其次,技术与组织双轮驱动的综合性 AI 准备度显著提高了应用概率,因此单一依赖技术投资并不足够。第三,对于生产复杂、高科技产品的企业,AI 实施的驱动力更强,管理者应将 AI 应用与产品特性、行业要求匹配,优先聚焦于提升效率、质量与创新的场景。最后,针对不同规模企业,本文建议小企业应强化准备度并寻求外部支持,中型企业可通过外部资源与合作伙伴克服资源瓶颈,大企业则需消除内部结构障碍,使 AI 应用与整体战略相协调。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1.本研究的 AI 准备度指数虽涵盖技术、组织及综合维度的关键因素,但未纳入伦理与社会性因素(如就业替代担忧、数据隐私风险),而这些因素可能显著影响员工态度与组织意愿。未来可以将伦理与社会性因素纳入 AI 准备度分析框架,结合更多技术与组织变量,形成更全面的 AI 应用分析模型。
2.本文假设技术性与组织性准备度为加性关系,未探讨它们之间及其子因素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未来可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方法分析技术与组织准备度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权重和关键驱动因素。
3.本研究中仅纳入部分市场环境与内部动态变量,未包括竞争战略、管理支持、风险偏好、财务资源等可能影响 AI 应用的重要因素。未来在模型中加入更多控制变量,细化不同规模企业(大、中、小)的差异化条件分析,提升对 AI 应用影响机制的解释力。
4.AI 应用被视为二元变量(应用/未应用),未反映使用深度、强度及其在生产环节的具体贡献。未来可以细化 AI 应用的测量维度,涵盖更多生产环节(如排班、任务分配)及其他职能领域(如产品开发、采购、营销),并评估应用的深度与效果。
5.研究仅针对德国制造业,结果的跨国普适性有限。未来可以开展跨国比较研究,评估制度与市场环境差异对 AI 应用的影响;同时进行长期跟踪分析,观察 AI 技术成熟和支持体系完善对应用曲线的推动作用。
6.本研究仅分析了实际应用 AI 的企业,未涉及未应用、应用失败、中途终止或未达预期效果的案例。未来可以探讨 AI 应用失败或放弃的原因,结合纵向案例研究分析实施过程中的障碍与关键转折点,并研究 AI 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智院微信公众号